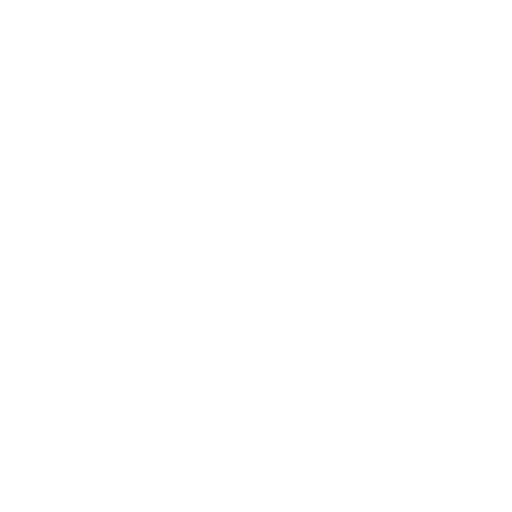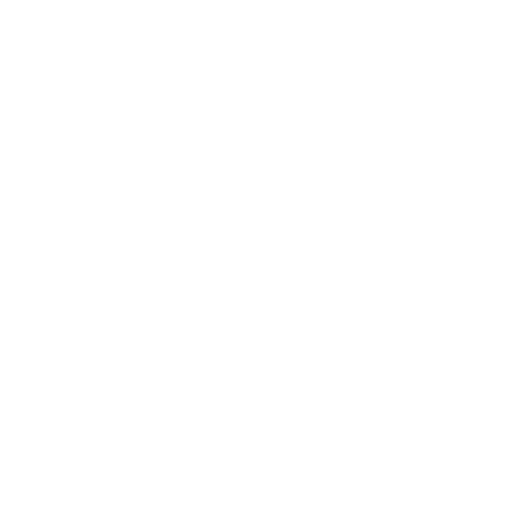17/02/2015
天價高更
我年少時在我家附近住了一個怪人,姓周,街坊稱他為「傻校長」。他的姑姐曾經在一幢唐樓其中一個單位開了一間規模很小的「卜卜齋」(幼稚園),先慈有一次告訴我我在那裏上過學,我完全沒有印象,是當年太小之故吧。
「卜卜齋」結業後,「傻校長」的姑姐留下自置物業給「傻校長」一個人居住。他的住所長年封塵,偌大的屋中間吊了一盞60火的燈泡,燈下放了一張四方枱和一張摺椅,枱上放了一部打字機。
他每天看書,用打字機做筆記,看的書全是西方大文豪的作品,海明威、約翰‧史坦培克、毛姆等等的書他全都看過,還用打字機將書中名句全部記下,厚厚一大本,他說這是學好上乘英文的最佳方法。
他甚少舉炊,每日黃昏時間總是借故走上我的家,先慈亦一定留他吃飯。他的唯一嗜好是打籃球,空閒時找我陪他玩一、二個小時。當年我比他長高一個頭,跟我單對單打籃球他很多時都食「零雞蛋」,後來我越長越高,他更加不是我的對手,最後他索性不跟我玩,走去找小學生跟他玩。
街坊說他念書念到「黐線」。他的家族開紡織廠,他是獨子,要繼承父業,念紡織的書本本厚如大英百科全書,念了幾年他終於精神崩潰,念不下去,他的母親於是接他回香港休養。
他的行為古怪,洗一條白色騎士牌內褲可以洗半小時,不停地用肥皂捽,過清水要沒有梘味才算合格,但他又從不打掃,一千多平方呎的地方處處都是厚厚的塵,洗手間更是隨處污垢,發出陣陣異味。
我當年年輕,只有十多歲,也用世俗的眼光看他,認定他「黐線」,年紀漸長才明白他可能患上「強迫症」。他的家教好,從不說污言穢語,對別人永遠謙謙有禮,常常保持一顆赤子之心。
他當年三十多歲,在我眼中卻像一個天真爛漫的小朋友,活在自己的童真世界。他的所謂家沒有電視機,他亦沒有女朋友,有時看書一看就是十多二十個小時,通宵達旦。有一次我用新學到的形容詞「eccentric」形容他,他先是愕然,想一想才哈哈大笑,說我的英語長進了不少。
Paul Gauguin’s 「When will you marry」
他介紹我看的第一本英文小說是以保羅‧高更(Paul Gauguin)的傳奇人生作藍本的《月亮與六便士》(The Moon and Sixpence),作者是毛姆(W. Somerset Maugham)。他說毛姆拿不到諾貝爾文學獎有它的原因,他的文字和故事確是沒有諾貝爾文學獎其中兩位得主海明威和約翰‧史坦培克的好和有啟發性,他借給我看的中編《老人與海》(The Old Man and the Sea)和《人鼠之間》(Of Mice and Men)我看了很多次,但當時年輕,我只能欣賞文字和造句,對書中故事的寓意,不甚了了。
中三那一年英文老師教念沙翁的十四行詩(sonnet)《永恆的夏日》(Eternal Summer),我背熟之後想在「傻校長」面前露露臉,誰知我念了第一句「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’s day」後,他竟然一字不漏地念下去。我覺得很困惑,一個如此熱愛和熟悉英語文學的人,為甚麽生活卻如張之洞一樣起居無節。
《月亮與六便士》的故事我印象深刻,當時不明白保羅‧高更為甚麼抛妻棄子,老遠跑到大溪地作畫。有一個故事說他有一次嫖妓,完事之後沒有錢支付肉金,妓女知道他是油畫家,叫他在木門後畫一幅畫當作肉金,妓女之後一直不在意,高更去世後很多年,他的畫價大漲,妓女將木門拆了,將在木門背後的油畫賣給一個收藏家,賣得的金錢足夠安享晚年。又有一次一個畫評家嘲笑高更的油畫謂「If you want your children to have a happy weekend, bring them to see Paul Gauguin’s paintings」(大意),因為他後期的畫作用色鮮艷及大胆,與傳統西方油畫著重光與暗的對比完全不同,而畫中人物多是歐洲兒童難得一見的大溪地土著。
高更與梵高一樣,都是難得一見的繪畫天才,亦同樣有一點神經質,分別是梵高自殺身亡,但兩人都是生前潦倒,死後畫作的價錢才大漲。
最近報載高更的油畫「When will you marry」以差不多3億美元賣給卡塔爾國家博物館,打破了另一位後印象派法國畫家塞尚(Paul Cezanne) 的「The Card Player」的世界最昂貴藝術品記錄。
卡塔爾政府豪花23億港元買入一件藝術品,據說是為了提升卡塔爾的國際地位及為迎接2022年的世界盃足球賽造勢,香港的M+藝術館豪花1.77億納稅人的錢,從單一渠道買入一籃子的當代藝術品,對提升本土藝術、香港的國際地位、普羅大眾的藝術品味有沒有幫助?
《經濟通》所刊的署名及/或不署名文章,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,並不代表《經濟通》立場,《經濟通》所扮演的角色是提供一個自由言論平台。
【你點睇?】政府將強制私家醫生須上載病人資料至「醫健通」戶口,你是否支持?► 立即投票